【抗战胜利80周年】弹片映山河:刘志才的烽火人生(原创小说连载)之 四[原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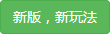
青峰侠 发表在 今日常德 华声论坛 https://bbs.voc.com.cn/forum-379-1.html
【抗战胜利80周年】弹片映山河:刘志才的烽火人生(原创小说连载)之 四
由刘志才口述,刘志才儿子刘建华(网名潺陵渔夫)校对,成方清整理撰
序
202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的荣光漫过神州大地时,我循着安乡县党史办、县文联、县档案馆的号召,踏上了安乡县陈家嘴镇的土地——此行的目的,是寻访抗美援朝老兵刘志才,记录他藏在岁月里的烽火故事。
在安乡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当地陈家嘴镇退役军人事务办与沙河社区居委会的协助下,我终于见到了老人。他的住处就在沙河社区,院坝里晒着刚收的稻谷,金黄的颗粒裹着秋阳的暖;墙角立着一把磨得发亮的锄头,木柄上的包浆,是几十年劳作留下的印记。九十四岁的他坐在藤椅上,脊背虽有些佝偻,双手却依旧稳实——指节因早年战场旧伤与常年耕种显得有些变形,却紧紧攥着一枚抗美援朝70周年纪念章。阳光落在章面上,折射出的光不刺眼,倒像一缕温柔的引子,勾着人想去听那枚勋章背后的人生。
老人话不多,每一句却都带着岁月的重量。他的人生脉络清晰而厚重:1931年生于这片土地(原梅保湖大队,今属保福村),8岁那年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他就主动去给乡邻放牛糊口,靠着帮工和乡亲们的帮衬长大;1950年,19岁的他报名参军,作为首批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在朝鲜战场历任侦察兵、通讯兵,两次冒死传递关键情报,荣立三等功,还在硝烟里火线入党;1964年退役后,他没选城里的安置,一头扎回陈家嘴镇的农田,后来又当村干部帮乡邻办实事,如今九十余岁,仍能铿锵唱响《志愿军战歌》。
朝鲜战场的冰寒,在他腿上留下了终身难愈的冻伤;悬崖坠车、泥土埋身的生死瞬间,也没磨掉他眼底的赤诚。他曾轻描淡写提起“7斤炒面守阵地两月”的日子,说夜里冻得缩成一团时,就摸出怀里揣的家乡泥土——那是出发前李伯悄悄塞给他的,“闻着土味,就像看见保福村的田埂,心里就踏实,就能撑下去”。这份朴素的念想,比任何豪言都更动人,藏着最纯粹的家国情怀。
整理这些故事时,老人的儿子刘建华(网名“潺陵渔夫”)给了我太多帮助。他翻出父亲泛黄的退伍证、旧照片,还有老人珍藏多年的半截钢笔——那是1952年圣诞节美军战俘营送的“和平礼物”,老人一直舍不得丢,说“要留着给娃们看,让他们知道和平来得不容易”。我们就这样,边听老人回忆,边记录细节,边补充过往,慢慢把“刘志才”这个名字背后的人生,凝练成了《弹片映山河:刘志才的烽火人生》这篇文稿。
写下这些文字时,我总想起老人院坝里的那棵老槐树——树干上还留着早年雷击的疤痕,却依旧枝繁叶茂,根深深扎在土里。这多像刘志才的人生:从战火里走来,把功勋藏在心里,把根牢牢扎进故土,用一辈子的坚守,活成了“守护”与“铭记”的代名词。
这篇文稿不是为了歌颂某一个人,而是想让更多人知道:我们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曾有人用青春、热血甚至生命守护;那些听起来遥远的峥嵘岁月里,藏着无数像刘志才这样的普通人,他们用一生践行着“家国”二字。
如果你愿意翻开这篇文稿,或许能听见一位老兵坐在田埂上的絮语——那不是传奇,是一个普通人用一辈子写就的故事。而我们愿意读、愿意记,便是对历史最好的致敬,对那些没能回家的战友最好的告慰。
成方清
2025年秋
第四章 鸭绿江边的风与机场
1951年2月,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4月11日,我们从辽宁丹东长甸河口跨过鸭绿江——作为第二批入朝部队,首要任务不是参战,是在朝鲜北部修建飞机场,为后续部队提供空中支援。
站在鸭绿江边,我望着眼前的江水:春寒未褪,江面上浮着零星残冰,江水泛着刺骨的凉意,远不像保福村边的河那样温和。对岸的朝鲜方向,硝烟裹着灰雾飘在半空,风从江面刮过来,砸在脸上像小刀子割肉,灌进衣领里,瞬间卷走棉服里的热气。我摸了摸怀里的布包,里面装着梅保湖大队的泥土——出发前,爹偷偷塞给我的,说“带着家乡的土,到哪儿都踏实,爹和你娘在家等你”。
“才娃,到了那边,先把机场修好,活着就是对战友最大的帮衬。”老班长拍着我的肩膀说,眼里藏着牵挂,“等停战了,咱们一起回各自的家,吃家里的热饭,走田埂上的路。”我用力点头,手指攥紧怀里的泥土,又摸了摸枪栓——枪托上还留着剿匪时磨出的细痕,现在要带着它,带着保福村的土,去更远的地方护着“家”。
过江那天,木船在江面上颠簸,江水溅在船板上,很快结成薄霜。我把棉帽的耳朵往下拉得更紧,还是冷得牙齿打颤。船行至江心时,我忽然想起保福村的田埂——春天一到,田埂边会冒出嫩草,娘会带着我挖荠菜,煮在稀粥里,鲜得能鲜掉眉毛;爹会在田埂上修水渠,准备插秧,汗水滴在泥土里,很快就被吸收。风裹着江水的寒气往脖子里钻,我把怀里的布包捂得更紧,泥土的腥甜透过布缝渗出来,像爹的手,轻轻拍着我的后背。
上岸时,冻土在脚下裂出细缝,踩上去“咯吱”响。部队驻扎在一片荒坡上,没有营房,大家连夜挖掩体——镐头砸在冻土里,只冒火星,震得虎口发麻。我的手很快磨出了血泡,血泡破了,沾在镐柄上,又冷又疼。老班长走过来,把自己的手套摘下来塞给我:“娃,戴上,别冻掉了指头——咱还得留着指头,回保福村帮你爹编草绳、扛锄头呢。”
修机场的日子比剿匪还苦。没有大型工具,全靠手挖、肩扛,石头重得压弯脊梁,冻土硬得能磕掉牙。白天,美军的侦察机在天上盘旋,大家得猫着腰干活,一听见飞机声就往掩体里躲;晚上,气温降到零下三十度,躺在掩体里,棉服冻得像铁板,连呼吸都带着白霜。我总把怀里的布包放在胸口,泥土的温度透过布层传过来,像揣着个小暖炉——我怕泥土冻硬了,怕再也闻不到家乡的味,怕再也见不到爹和娘。
有天清晨,天还没亮,大家正埋头清理碎石,敌机突然来了。
“卧倒!”老班长喊着,一把把我按在掩体后。炸弹在不远处爆炸,碎石子像雨点般砸下来,我感觉胳膊一阵火辣辣的疼,伸手一摸,血渗了出来。我第一反应是摸怀里的布包——还好,布没破,泥土还在。
晚上,老班长用盐水给我清洗伤口,疼得我龇牙咧嘴。“傻小子,命比啥都重要。”老班长叹着气,从自己的干粮袋里摸出半块炒面,“吃点,补补力气。这炒面还是国内带来的,跟你娘煮的野菜粥比,差远了。”我嚼着炒面,没说话——我想起娘煮的粥,虽然稀,却暖;想起爹烤的红薯,虽然小,却甜,现在想起来,比啥都香。
战友里有个叫小李的,才十七岁,河南人,想家想得直哭。我把布包打开,倒出一点泥土,递到小李手里:“闻闻,像不像你老家的土?咱好好修机场,等空军来了,把美国人赶跑,就能回家了。”小李攥着泥土,眼泪掉在泥土上,点点头:“刘哥,我听你的,咱早点回家。”
可小李没能等到回家的那天。半个月后,一场轰炸中,小李为了保护刚运来的钢筋,被弹片击中了胸口。我冲过去时,小李还攥着那点泥土,嘴里念叨着“娘,我想回家”。我把小李手里的泥土小心地收起来,和自己的混在一起,包进布里——我想,以后不管走到哪,都带着小李,带他回“家”,回那个有田埂、有热饭的地方。
作者声明:本帖为本人原创,未经本人和华声论坛许可,不得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