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不过恍惚间[原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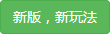
欧阳杏蓬 发表在 荷韵轻香|散文 华声论坛 https://bbs.voc.com.cn/forum-5-1.html
所有不过恍惚间
吃过晚饭,客人走后,母亲收拾桌子,收拾了一小袋骨头和其他食物残渣,加上厨房里一些不要的剩菜——一点放了几天的炒血鸭,半碟鱼冻,凑成了一小袋。母亲拎着,言说丢到门口的小河里,让水冲走。我一听说要扔河里,不愿意了。门口是龙溪,我放鸭子的时候,龙溪水清凌凌的,纺纱织布一样顺溜的流向南面水田。而前几天,遇到平田村里的长辈,他都要号召大家下河清理河里的垃圾了。龙溪已不像溪,像臭水沟了。这让把龙溪引以为母亲河的平田人,着实难堪了。其时,我在场,我也看到过门前水泥桥下的河湾里,不仅有生活垃圾,水里甚至还漂着一条小狗的尸体,狗毛在浮在水面,如水草。另一个大叔在河堤下也发现了堆成堆的鸡毛、鸭毛,浮肿的眼泡里,闪出忧郁的光。
我们都不希望龙溪变成臭水沟。
我伸手要过母亲手里的塑料袋子,说:我丢到屋后面的竹林里去。我下午看到了大伯伯的几只猫,在竹林里鬼鬼祟祟。
大伯伯去年九月去世之后,大伯母跟着孩子去了县城住,家里几只野惯了的猫,别说带走,抓都抓不到。大伯母在县城住了几天,说县城里的巷子一模一样分不清,楼上的门一模一样认不清,又闹着回来。回老家,脚踏实地,熟门熟路,自如,自在。大伯母回来了,她的几只猫不听她叫唤,习惯了在竹林里和竹林边的山石里盘桓了。我最多一次见过三只,在竹林边的山石下的干枯竹叶上,小心翼翼,却在自由的爬行。它们没有发现我,而我,却观察了它们好一会,还让弟弟来看——我还以为是野猫。
我提溜着袋子,走过九哥门口——九哥是村里唯一不上床睡觉不关大门的人。门前空地上,一只火炉孤零零蹲在路灯下。九哥大门敞开,堂屋里开着灯,不见人影。绕过九哥的屋角,九哥的屋,已经是三层楼的房子,抬头,居然是黑天。还好有灯光,巷子石板上的东西,依稀可辨,土坷垃,土砖头,废柴,干枯了的草,再往里,是九哥的哥哥搬走后留下的宅基地,并不空空荡荡,里面小苦楝树、灌木、何首乌藤子,交织成密密实实的一片,在暗光里,神秘莫测。再往里,就是竹林,安安静静的竹林,并没有猫叫的竹林,白天并无异象的竹林,此时,却像个堡垒立在面前,竹尾稍挤在一起,像在交头接耳了。
这一片本来住着三户人家,最东一户,石狗老伯,东干脚脾气最好的男人,被老婆欺负,被兄弟欺负,还被平田人闯进家里欺负,忍辱负重,经营着一大家子人的生活。五十岁的时候,在自留地建房,搬了出去。几年下来,老宅不堪重负,屋脊塌陷,四面墙受够风吹雨打后,日渐坍塌,又几年,瓦砾中长出了毛竹——不知是石狗老伯孩子有意手植,还是他的兄弟特意为之,但石狗伯伯是断然做不到的,因为那时,他已经中风瘫痪,出门坐在轮椅上,要昔日凶他的婆娘推了。他的婆娘因为他瘫痪而母性大发,但无力回天,熬了两个年头,石狗老伯向疾病屈服,一睡不醒。当年,每到初冬季节,石狗老伯就在门前支起蒸锅蒸酒,整个村子都是红薯酒的味道。我放牛过路,石狗伯伯佝偻腰,叫住我,在酒缸里打一小竹筒新酒,要我尝尝他的酒。他那种自得,犹如他蜡黄脸上的桃花。他怔怔看着我,两眼出神的样子,如在眼前。
竹林边的空地,是真叔的老宅基地。真叔娶了老婆后,奋力经营田地,没赚到钱,又学砌匠,学会之后,自己动手,在村前的责任田里下了基脚,先给自己建了楼房,搬了出去。原来的老房子被搬空了,板壁也被抽掉了。两年雨水,老宅旧物只剩几堵墙脚。原来的厅堂卧室,现在何首乌简直为所欲为,不仅在里面相互倾轧,水泼不进,还长出来了,铺到九哥后面的巷子里了。脚下的巷子,小时候砸泥巴,长大一点下五子棋的石板,在暗光里,只能见到一角,如脸,周边披覆的尘土,如发。真叔发家之后,励精图治,力争做个农村里的种田能人,收割机、插田机、烘干机、犁田机……样样置备齐全,用力过度,于某个夏天正午扑跌在田头,一头泥水,便向这世界做了告别。我会骑自行车,就是真叔当年把着单车龙头,在晒谷坪上教会我的。他掌着龙头,跟着车跑,还推着我,头发被汗水打湿贴在前额上,脸上汗津津,两眼深邃的看着前方,一边喘气的样子,好像就在何首乌盖住的墙根边,他倚在断墙上歇气。
这吓了我一跳。
真叔死的时候,父亲特地给我打了电话,说村里情况不妙,年轻人、中年人接二连三的死。一向胆大不信邪的父亲,都胆怯了,要我平时注意一点。真叔死的时候,还不足五十岁,正是力大如牛的时候。
再往边一点,是村里一绝户留下的宅基地,真叔生前,在那宅基地中央,种了一棵公孙树。抬头看看,公孙树长得已经高过九哥的三层楼房了,光秃秃的,孤零零的,抵挡着后面凌厉峭壁的威压逼迫。
我还没走到竹林,大约还差一根扁担远,便把手里袋子向着竹林里扔了过去。
绝户两口子,我当年是见过的,在村里口碑不好,无人问津,男的死后,女的上吊。上吊时穿了老衣老裤,戴着一顶新的黑纱帽,脚穿黑布鞋,一心赴死。现在想起当时那女的挂在门框上的样子,心里却毫无波澜。
石狗伯伯带我去永安圩挑过豆子,他馋鸭头的样子,我现在还记得,舌头在嘴唇上舔了又舔,眼睛都要掉出来了,由于惧内,始终没吃成。
真叔的父亲母亲——也是石狗伯伯的父亲母亲,我也见过。真叔的父亲先逝,脸像一张擦锅的抹布,在我印象里,一直是扭成一团的,还黑。好抽烟,死于肺病。他的那根竹烟杆,被他摸得油光滑亮。真叔的母亲信仰各种偏方,紫苏蒸蛋、苋菜补血之类。一次用活鸡泡酒,埋于地下三尺,足月取出,一坛子,连鸡带酒,分三天食用,不知道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肝被感染了,看了很多草药医生,无果,去正规医院,当天去,当天回,吐了很久,一屋秽气,用了一大瓶花露水都不起效。在众多子女的呼天抢地中,真叔的母亲最后在一屋秽气中撒手而去。去时眼窝深陷,颧骨高耸,状若骷髅。她在世的时候,每年家里收了拐枣,都会给我母亲送一小篓子。她需要的回报,仅仅是几句好话。
走出巷子,九哥撅着屁股,正往炉子里吹气。
他说他还没洗澡,烧一锅水洗澡。
九哥,这个当年带我走十几里地上大岭砍柴的年轻人,转眼之间,就七十多了!
我安顿了一下慌张的内心,想跟九哥扯几句,却找不到话。我家跟他家,一墙之隔,以前是经常跟在他屁股后面,听他讲各种江湖故事的,现在居然无话可说!九哥吹燃了炉火,坐在小凳子上默然,路灯光下,九哥歪戴着一顶油腻的帽子,一脸平静的专注的看着炉火。他很清瘦,脸上已经无肉。他在想什么?想他三十岁还在单身的儿子接下来会有条什么样的出路?还是在想如何安顿他疯疯癫癫的老婆?我想,他唯独不会想他自己以后怎么样。
我伸手给他递烟,吓了他一跳。
他接了烟,只稍微抬头看了我一眼,并没有感谢我,一边伸手抖抖瑟瑟地在炉里捡出一根燃着的柴火,一边板正地对着前面夜空说“天无绝人之路,船到桥头自然直。”
母亲在门口叫唤我,我丢这个垃圾丢得太久了。
我听到了竹林里发出了哗啦哗啦的声响,猫在行动了。
九哥点了烟,并不吸,抱着膝,在路灯光下,缩成了一团,要缩进地里了。
我没有回头,也没有声响,我得适应这人世。人生一世,如白马过隙,瞬间烟花,刹那芳华,最后空空如也。生与死,不过恍惚间。恍惚间,我看到了那一张一张熟悉的脸孔,在眼前一个一个消失。沉默良久,我想,唯有热爱生活才能在这山地里坚持,唯有坚持可抵岁月漫长。
2023.1.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