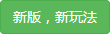|
帖子主题:当郭兰英遇见“喜儿”[下载]
|
|
发表时间:2023-8-17 14:40
当郭兰英遇见“喜儿”[下载]
|
|
回复时间:2023-8-17 14:41
1947年,郭兰英进入华北联合大学戏剧系学习,在一年多的学习时间里,郭兰英魂牵梦绕的《白毛女》有时候会演出。在老解放区,郭兰英上课的时间更多,演戏比较少。但凡演出《白毛女》,郭兰英就跟着剧组,一边负责杂务,一边在乐队里顶个数。她回忆说:
我又管服装,又管道具。不过,也没有多少服装。就跟老百姓借,把我们军服给人家穿,老百姓还不干,人家就那么一件衣服,你再拿走了还行?实在话,穿完以后,咱们再把军服拿回来穿在身上,说不定里头就有虱子、虮子了。但是没办法,那个时候只能借。 服装办妥了,我还管打击乐器,还得看戏。 我的表现不错,挺好的。 郭兰英说:“那时候,学会了乐器,拉二胡、板胡。不过,我板胡拉不好,因为那个弦绷得太紧了,不好学。我就拉二胡,打梆子,锣、鼓、镲这都得要会,文工团嘛,缺什么顶什么。”就这样,郭兰英把《白毛女》看会了,每句唱,每句台词,每个动作。她甚至想,如果自己上台演,应该如何。 1947年11月12日,人民解放军攻克石门,石家庄解放了。在小李庄扭了一段秧歌之后,郭兰英随军进了城。 在石家庄,华北联合大学文工团把一台《白毛女》奉献给石家庄市民。 有一次,已经登报做了广告,要演出几场《白毛女》,群众非常期待。临到演出,扮演喜儿的两个演员,王昆和孟于都上不了场。郭兰英回忆说: 本来两个演员倒替着演,结果一个演员病了,王昆吧,怀着(胎)七月,要生孩子了;另外一个演员临时出去没回来。海报登出去了,没办法,领导挺着急的。“怎么办?改期吧?” 正在他们研究的时候,我就在外边报告,说:“团长,我愿意演出!” 团长和导演说:“你演出,你什么时候学会的?” 我说:“我在前台搞打击乐,都看会了。要不然,我演一下,你们看一看?” 在食堂里头弄了个空场,我就给他们演了“北风吹”那一场。一演,一点儿都不错。领导就决定让我演了。 真正上了舞台,郭兰英的戏确实非常精彩。可是,到了最后“斗争会”,她的情绪完全不由自己控制,哭得稀里哗啦,演出无法正常进行下去,她回忆说: 一开“斗争会”,我想起“斗”我师娘的情景。一想到我师娘,我就唱不下去了,就哭啊哭的。乐队有时候拉一下,有时候就停下来等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导演着急了,他特别着急,说:“兰英同志,兰英同志,这是演戏!”但是我止不住,怎么也演不下去了,哭得怎么也唱不出来了。导演没办法了,指挥合唱队一起唱,斗争黄世仁,含口号,完了,我就下来了。下来之后,我趴在桌上还哭,导演过来说:“别哭了,别哭了。” 《白毛女》第一次演出,就闹了这么一场。 虽然还有几句唱没有完成,但是郭兰英演喜儿的潜在能力终于释放了出来,所有人都看在眼里。于是,她理所当然地成了又一个“喜儿”。郭兰英回忆说: 我这人有个最大的特点,也是致命的缺点,就是倔,很倔。有的事情我接受不了的话,绝对不接受,不干。而我好的一点是,特别聪明。第一次演《白毛女》,导演就肯定了,可以演。只是每一次演到“斗争会”,就老想哭。 所以,每次到“斗争会”的时候,大伙儿就启发我,合唱,说:“喜儿,咱们一定要斗争!”很多群众的戏也加进来,这样就好一些。 第一次演出得到了领导的肯定,然后就加上了我,A、B、C三个“喜儿”,我是C。 三个“喜儿”,王昆是A角,孟于是B角,郭兰英是C角。 孟于记得,“一般是今天她演明天我演,重要的演出是王昆去演”。孟于印象中,郭兰英性格开朗,非常好,她不仅能喝酒,爱喝酒,而且还能喝很多。做了C 角,郭兰英也心直口快,开玩笑说:“我原来就是‘头牌’了,为什么演《白毛女》排在老三啊?” 听罢,大伙儿都乐了,因为在革命队伍中,“头牌”早已经不是褒义词了。 演出没有像样的舞台,随便一个广场上,找一个略高出地面的土台子,就可以表演。郭兰英说:“到哪里演出,拿土垫起来半米高的一个舞台,就等于这样跟老百姓近距离地演出,所以老百姓看得清清楚楚。” 《白毛女》演出时间相当长。郭兰英记得:“下部队去演出的时候,从天黑一直演到第二天太阳出来,真是太阳出来的,五个小时嘛。这么长时间,观众都坐在地下不走。” 有一场戏,郭兰英说,起码得演40分钟。这场戏里,“还要生‘小白毛’。山洞里头还要喂奶啊;没有奶,吃雪,把那个雪抓起来,塞到嘴里头,把雪融化了以后喂‘小白毛’”。 革命文艺舞台锤炼了郭兰英,给了郭兰英艺术以新的生命,但是,郭兰英又把传统戏曲基础巧妙地融会在革命舞台上,使之服务于新的歌剧艺术。 郭兰英回忆说: 我脑子里想的,就是怎么能把戏曲的动作用到歌剧里,但是又让人家看不出来你是戏曲里边的,目的要做到非常感人。 比如,唱“北风吹,雪花飘”,开门、关门的动作,就把戏曲当中能够用的动作都加到里头。农村的门就这么大,你超过了这个,就假了。 还有戏曲跑圆场。在“逃走”一场戏里,黄世仁和穆仁智追,我就跑圆场。但也不像戏曲里面的圆场,一边害怕,一边看着后面,怕追来,然后往前跑。导演肯定了我,我自己做得也挺舒服,所以就确定下来了。 喜儿被黄世仁侮辱以后,有一场戏叫“黑虎堂”。一开始,导演排的是:出来以后,在那里哭啊,埋怨啊,“娘生我,爹养我,生我养我为什么?”站着唱,唱着唱着“娘生我啊”,我这腿就想跪下来,“生我......一下就跪下去了,“生我养我为什么”,拍着腿就在那里哭。整个乐队拖得也太长,然后,“这,这”,又自然而然地站起来,“这叫我怎么有脸去见人?”“这叫我怎么......”一跺脚这个动作,原来是没有的,这都是戏曲的动作,我拿到这儿。 就这一跪,给人印象深刻。大家把这些手法归纳为郭兰英舞台艺术实践中的独特创造。孟于回忆说:“郭兰英同志在演出当中,她有创造。她不一定按导演要求的做,她到台上能够自由发挥。特别是《白毛女》第二幕,黄世仁强奸了喜儿出来以后,我们都没有跪在地上唱的,她那天唱这一段的时候,唱到最后‘爹啊,娘啊’,就一下子跪在了台上。当时大家都很惊讶,但被她带进了戏里。后来导演也同意了。” 虽说是三个人演,但“喜儿”只能是一个。在贺敬之看来,三个演员基本的东西是一致的,就是都身为革命文艺工作者,内容第一,认真塑造形象,不是演自己。 虽说是一个“喜儿”,但表演又有不同。贺敏之说,郭兰英很自然地运用了戏曲的表演程式,但又不是生搬硬套。如果完全像最早排《白毛女》一样,彻底恢复旧戏中花旦的表演,那绝对没有郭兰英。贺敬之说: 郭兰英给我第一个艺术印象,就是演到“黑虎堂”,出来唱“娘生我,爹养我,生我养我为什么?”声音高亢,充满了感情和激情。演到这里,她突然跪下了。这是原来没有的,延安时期演出没有,后来王昆演出也没有这个。这就是郭兰英自己的风格。 另外,作为艺术家,她充满激情,非常动人。她的唱腔、发声、声音表情,都有自己的特点,有自己的风格。除去她聪明,肯学习,以及过去戏曲的功底外,就是她一直追求革命,是有革命情绪、革命热情的。她没有走邪路、弯路,是名副其实的新歌剧艺术家。要演革命的艺术,必须自己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 舒强在延安就开始执导《白毛女》,这时又是文工团团长、导演。面对新人郭兰英,如何把这个“喜儿”打造好,舒强发挥了自己的优势。 舒强在重庆搞过话剧,还钻研俄国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戏剧理论。他和郭兰英是两种舞台呈现的思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理论基础是强调“体验派”:“要学习、观察、倾听、热爱生活。”演出应该深入研究人物形象的生活逻辑。而郭兰英所受的戏剧教育中,一切都是规定好的,即程式化的一套。那一个时代的革命者,不少人还没有细细研究传统戏曲的美妙,首先是扬弃其视觉上较为陈腐的一部分。 在扬弃和吸收之间,郭兰英自如运用程式化和舒强的“斯坦尼”一结合,就有了一个完美的“喜儿”!郭兰英说;“舒强同志对我帮助太大了,他强调从人物出发,说‘你不要演戏’。”本来就是演戏,为什么又说“不要演戏”呢?这就是“斯坦尼”理论。舒强启发郭兰英“创造人物”。郭兰英回忆说: 我从舒强那儿有一个最大的体会,演戏要从人物内在灵魂出发。他说,是你演人物,你就要把那个真实的形象演出来。我跟他说:“舒强同志,是不是从人的灵魂出发?”他说:“好,好。你自己演唱要从内在心灵出发,这就对了。” 舒强用“斯坦尼”理论来说服郭兰英,要求从“喜儿”这个人物的感情出发,不能是郭兰英本人,如果演郭兰英,永远演不好。他说:“你就把郭兰英当成当时的喜儿,你怎么处理,这不就很具体了么?”郭兰英这下明白导演的要求了,她说: 整个《白毛女》,喜儿一开始是17岁的小姑娘。到了地主家里头,又高了一层,年岁又长了,我把她处理得大了两岁,更成熟些。成天地挨骂挨打,就逐渐成熟了。 最后,逃出黄家,在山洞里,就已经是什么都懂的中年人了。想到这些,在表演处理上,再往里头一点一点深入。根据自己的声音,把自己的声音修理一下。 舒强同志老说:“你自己体会,你演的这个角色是什么样的人?你应该怎么样来演这个角色?”听他讲课,听他在排演场上给你分析,特别有收获。 上了舞台,脑子里头整个思维就投入到这个人物当中了,我就是这个人物,不是郭兰英。如果一上去,让观众都喜欢我郭兰英唱,完蛋,肯定就完蛋! 郭兰英至今都觉得她不能把舒强的分析说清楚,但她可以体会到,能够感悟到导演的意图。一举一动,都根据人物心得来表演。比如《白毛女》“跪”的动作,郭兰英事先不仅没有设计,也没有想过。她说:“确实是感情达到了一定的程度,我自然而然地就跪下去了。” 笔者:提前没想过? 郭兰英:没有。一点儿都没有想,就是那次进入角色,不是第一次演,演了好多场了。原来都没有跪。 笔者:大家都觉得震动很大? 郭兰英:跪下去唱完以后,噢,知道了,我怎么跪下去了?后来自然而然地边唱“这叫我怎么......边往起来站;起来了,继续唱:“......活?” 笔者:自然而然地起来了,不露痕迹? 郭兰英:嗯,很自然。唱“娘生我,爹养我”跪下,因为拖得很长,很适合当时喜儿的状况和环境,还有心里头的矛盾状态。你说跪下去了怎么起来?这个时候我倒没怎么想怎么起来,也是很自然地就起来了。“这,这,这叫我怎么有脸去见人?”然后,唱“这叫我......”一下站起来了,“......怎么活”,趴到桌子上。 郭兰英提心吊胆从台上下来,以为团长、导演舒强要批评她,骂她:“你怎么就跪下去了呢?”结果,舒强说:“好!好!处理得非常好!” 为什么好?就是两种理论有机地融合在了一起,创造了新的惊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