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绒蒿[下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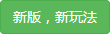
computer2014 发表在 科学探索 华声论坛 https://bbs.voc.com.cn/forum-148-1.html
那次果洛之行,让我见识了来挖冬虫夏草的艰辛——那些远道而来的农民和当地的牧民,匍匐在海拔近5000米的高地上,肌肤紧贴在尚未解冻的泥土上,在呼啸的寒风和不期而至的冷雪中,手持一把小钁头,目不转睛地盯视着前方,希望从刚刚萌芽的青嫩牧草中辨识出一只冬虫夏草来。而在此时,一只冬虫夏草从众多牧草中闪现出自己的身影,让这些在苦寒中等待希望的人们眼前忽然一亮。这也几乎顺应着绿绒蒿们的用心——她们攀援到更高的高处,把她们的美丽,留给了空寂的天空与大地,谢绝了人们的欣赏和赞美。而愿意追逐她们的人们,则要历经路途艰辛、高寒缺氧以及刺骨的风雪,才能够碰触到她们的美丽。
那次果洛之行的另一个收获,是知道了那种金黄色花儿的名字——全缘叶绿绒蒿,以及她的藏语名字——欧贝勒。已经不记得她的汉语名字是谁告诉我的,只记得他还告诉了我全缘叶绿绒蒿的一个秘密:她们之所以选择在草原一片荒芜的季节开放,让花瓣闪耀着酥油灯一样醒目的金黄色,就是想着让那些经过一场冬眠,与她们一起苏醒过来的昆虫们——那些熊蜂、蝇虫和蓟马能够在第一时间发现她们,给它们提供花粉,让它们辘辘饥肠得到温饱的同时,也帮助她们传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她们也是煞费苦心,她们让太阳为她们帮忙,用强烈的紫外线照射她们,让她们个个有一张色彩鲜艳的容颜。
绿绒蒿的藏语名字,则是一位正在采挖虫草的牧民告诉我的。当时他刚刚采挖到一只虫草,满面欢喜,一边轻轻搓揉着粘在虫草上的泥土,一边指着不远处的一朵全缘叶绿绒蒿,用带有四川色达口音的藏语对我说:“这是欧贝勒,是欧贝勒赛布,等到了夏天的时候,还有欧贝勒玛布、欧贝勒昂布盛开起来,太好看了!”我知道,置于欧贝勒后面的赛布、玛布、昂布是藏语黄色、红色、蓝色的意思。也就是他的这句话,促成了我在次年的6月中旬,再次来到了果洛草原。这一次,我专门带上了相机,也带上了我通过查找资料获得的知识,记事本里还夹着刚刚发行不久的一套特种邮票《绿绒蒿》。正如那位采挖虫草的牧民所说,我见到了开着红色花儿的红花绿绒蒿、略微泛紫的久治绿绒蒿。那是一种单纯的红,没有一丝杂质,恰如牧人身上佩戴着的珊瑚玛瑙,有一种坚定和果断的美,但她却又薄如蝉翼,阳光照射在花瓣上,瞬间变得通透,难以想象这样单薄的花瓣是如何抵御高原上的风雪的。也见到了开着蓝色花儿的多刺绿绒蒿、总状绿绒蒿。那是高原紫外线把蓝天融化之后,注入了她的花瓣,我也打开我想象力的阀门,想象她们是喜马拉雅古海洋遗落在草原上的宝蓝色浪花。而此时,金黄的全缘叶绿绒蒿正在退场,花瓣已经消散,花萼的地方结成了果实。显然,作为一朵花,她已经完成了她的使命。她们的颜色,也变成了她们刚刚开放时,围拢着她们的牧草枯黄的颜色,有一种功成名就之后,完全放弃了对盛名的执着的随意和轻松。我拿着相机不断对准一束束花儿,把那一抹抹红和一抹抹蓝都留在了我的相机里,也把干枯了的全缘叶绿绒蒿定格在了相纸上。
这一次,我还把“欧贝勒”这个名字记在了我的记事本上,也记下了她们各自不同的颜色。回到省城西宁,我开始按图索骥,查找资料,猛然发现,“欧贝勒”这个词来自梵语,也就是在汉译佛经经典籍中时常提及的“优钵罗”(亦写作沤钵罗等),也就是说,“优钵罗”是“欧贝勒”的汉语谐音写法!然而,在梵语里,“优钵罗”指的是睡莲,是一种水生草本植物,一般适于生长在热带或亚热带地区,在青藏高原高寒地带难见其踪。在汉译佛教典籍中,“优钵罗”也被译作青莲华、红莲华等——佛书认为“花华不二”,所以一般称花为华——那么,她在牧民的口中,怎么变成绿绒蒿了呢?绿绒蒿是罂粟科绿绒蒿属植物,与水生植物睡莲相去甚远。此前,绿绒蒿缘何选择了海拔更高的地方生长这个问题还没有明朗,这样一个问题又接踵而来。
一次, 也是在果洛,与藏族母语诗人居•格桑闲聊,我便向他请教这个问题。他的一席话让我豁然开朗。他提及了佛教从印度传入青藏高原的那个久远年代。
伴随着佛教供花仪轨的传入,以睡莲作为主体的供花仪轨演变成了绿绒蒿,原本出现在佛教里的睡莲的名字“优钵罗”,也从经卷里走出来,走进了牧民的口语里,高原野生花卉绿绒蒿自此更名换姓。如此,对青藏高原来说,睡莲,便成了绿绒蒿的前世,或者说,初传佛教的青藏高原借此完成了一次“借花献佛”。那么,作为一种高原民族耳熟能详的常见高原花卉,如今被藏民族广泛叫作“欧贝勒”的绿绒蒿此前叫什么名字呢?出于好奇,我曾向被人们称为“鸟喇嘛”的扎西桑俄堪布请教。没想到,我的疑惑,也曾经是他的疑惑。几年前,他就曾通过实地和网络在西藏、青海、四川等有藏族聚居的地区进行探询和调查,得到了答案,他把他的调研结果发给了我。绿绒蒿“欧贝勒”果然曾有过她们美丽的名字:全缘叶绿绒蒿叫嘎玉金秀,红花绿绒蒿叫阿达喜达,蓝花绿绒蒿叫喜达昂波……
然而,高寒的青藏高原不可能在一年四季里持续满足供花的需求,尽管以替代的方式解决了高原不生长睡莲的问题,但在漫长的冬季里,包括绿绒蒿在内的众花衰败,这一仪轨依然难以为继。
如何让供花的仪轨保留下来,让那些信奉佛教的信徒们在佛前表达虔诚之心呢?
多年以后,我去塔尔寺采访。春节刚过,元宵节就要来临,塔尔寺的两个花院——上花院和下花院正在马不停蹄地加紧制作酥油花,以便在正月十五月圆之夜,向游客和信徒展示他们的酥油花工艺,得到他们的观赏和瞻仰。我被特许进入了制作现场。
酥油花,最早起源于西藏苯教,一种叫“多玛”的祭祀品系用青稞糌粑捏制而成,其上粘贴着工艺简单的酥油贴花。因为只是用于祭祀,这种叫“多玛”的制品也只在很小的范围和场域存在,甚至在制作与使用时,有一些有意掩映的成分,所以并不为人所知。然而,它又是如何成为塔尔寺等各大寺院一种专门由艺僧制造、广为展陈的佛教艺术品的呢?
我曾想象,那应该是一个曾经制作过“多玛”的艺僧,改信佛教后,他对佛教虔诚有加,经常奉行着供灯、供水的仪轨,但也对高原隆冬季节不能在佛前供花耿耿于怀。一日,应该是清晨,这位艺僧起床诵经,接着便开始用早餐,那天他吃的是用酥油和炒青稞粉拌制的糌粑,当他从糌粑木箱里拿出一块酥油,就要放入碗中,早年制作“多玛”的技艺在他的指尖复活,他随手就捏制出了一朵酥油的花朵。看着在指尖上忽然盛开出一朵金黄的花朵,这位艺僧忽然想到了什么。“梅朵乔巴!”艺僧忽然叫了一声,放下了还没有吃完的早餐,便出了僧舍,径直朝着大经堂走去,出门前,带上了他仅有的一坨酥油。
“梅朵乔巴”便是供花的意思,这位艺僧到了经堂,便用酥油捏制了几朵花儿,供奉在了佛前。如此,酥油花应运而生。藏民族至今把酥油花叫作“梅朵乔巴”。
酥油是从牦牛奶中提炼出来的,是高原上营养价值极高的一种食材。牦牛的产奶量本来就没有多少,从牦牛奶中提炼出的酥油也就显得极为珍贵。然而,用酥油制作酥油花,再把它供奉在佛前的习俗一经开始,便得到了青藏高原广大寺院和民众的纷纷效仿、响应,很快,每一座寺院都有了供奉酥油花的亦轨。这是因为,酥油花的出现,解决了深冬季节不能用自然生长的花卉供奉的遗憾。尽管这种食材是那么全贵,但比起他们内心对佛法的虔诚,这又算得了什么呢?如此,酥油花便成了欧贝勒——优钵罗的像生花。
如今的酥油花,也不单单只有花儿——酥油有着极强的可塑性,于是那些艺僧便用酥油捏制成了更多的工艺形象,其中,有人物,有山水自然,有亭台楼阁,整个儿构成了一段故事,就像连环画一样,讲述着佛经中那些耳熟能详的故事。而在各种内容的间隙里,依然布满了各种花卉。每一朵花儿否富丽、繁盛,就像是自然界的花儿恰好盛开到了极致,把自己最美的瞬间展示了出来。
那一天,我看着那些花儿,问我身边的小僧:这些花儿都是什么花儿?小僧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欧贝勒!
听着小僧的回答,我感到我的脑际忽然嗡嗡作响。欧贝勒——优钵罗,这是绿绒蒿从印度睡莲那里盗取的名字,但她又不能像睡莲那样四季开花,时时供奉在佛前案上。于是,酥油花替她完成了广大佛教信徒的心愿。或许,我看到了绿绒蒿的今生,或许,这又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借花献佛。
藏民族生活在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地方,长期与高寒缺氧共存,形成了独成体系的生存智慧。他们深知高原生物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的不易,并且也敏锐地察觉到大自然诸种物种之间相互共生又相互制衡的道理,形成了自己朴素的生态理念。小时候,父母从来不让我们采摘野花,说那是大自然的头发。“如果我薅了你的头发,你不疼吗?”有一次我摘了一捧野花带到家里,被我母亲看见后,她便说了这句话,这句话我至今记着。记得在我的家乡,每每到了盛夏季节,野花盛开,那些牧民和僧侣面对着漫山遍野的鲜花,便开始虔诚地诵经祈请,口中低呼“供奉三宝”,但不去摘采花儿,用意念把这些花儿供奉给自己信奉的神灵。这,也是一种借花献佛啊!
绿绒蒿到底有多美,这一点,从那些西方人第一次见到绿绒蒿后的惊讶和赞叹可以看出。100多年前,许多的西方人——探险家、传教士以及植物学家涌入喜马拉雅山地区,发现并采集了各种颜色的绿绒蒿,这其中有后来成为世界上享有盛誉的植物学家的洛克、金登•沃德、威尔逊等,他们赞誉绿绒蒿是“喜马拉雅蓝罂粟”。凡是初次邂逅这种花的人都会为它疯狂。自此,西方人大量采集绿绒蒿的种子带回西方,并在西方园林驯化培育出了绿绒蒿,绿绒蒿很快成了西方园林里的最宠。
如今我国许多地方也开始驯化和培育绿绒蒿,希望这种美丽的花儿也能成为我们城市园林的绿化和观赏植物,不要让她总是开在深山无人问津。率先传来好消息的是西藏和云南,但这并不奇怪,西藏和云南原本就是高原,让一种高山野花在高原园林得以开放,可能相对容易一些。而当我听到北京植物园成功地栽培出绿绒蒿的消息,内心还是掀起了欣喜的微澜——我一直有一个想法,比如我所居住的城市西宁,是青藏高原最大的城市,有朝一日能够以高山花卉作为城市绿化植物,以此吸引四方来客,而不是像现在一样,大多是引进一些毫无地域特色的外来花卉来美化这座高原城市。如此,也可以算是这座城市的一种生态标签吧。绿绒蒿在北京初次绽放,这是她首次在平原露地栽培成功,相对于北京,西宁应该更能够让绿绒蒿盛开起来。或许,这才是绿绒蒿的今生、抑或,是她的未来。